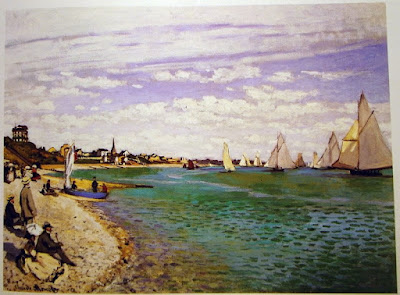當代繪畫的風景語言——從「去地域性」到「再地域性」 (de-territorialized to re-territorialized)

鄭在東,《丹鳳山》(油畫,1993) 當我們談論風景繪畫,不可避免地需先說明平面作品的虛幻性。首先我們身處的真實世界是由空間與時間所建構,繪畫卻因合理的虛構與再現而成立,換言之,繪畫空間與真實世界相對即是種虛構和幻象。更加有趣的是,因為繪畫經過現代化階段——試圖將歷史所有的內涵加以破壞,純粹因為想要定位在「現今」的視點,以致當代對於繪畫的立足點,也能接受源自「虛構」而成的觀點。那麼因為虛構帶來的自由性,所以稱呼(或說虛構)當代風景畫為一種語言,也就不為過了。何況繪畫是由畫家的心象發想而成的,目的是為了把相當複雜、重要的概念藉由媒材來傳遞,其特性與「語言」無異,都擁有交流觀念、意見、思想和含義等作用。 新的風景繪畫具有「可辨識性」、「可溝通性」的特性,它表現出來的並非單一事物,僅以一種看它的方式是不足的,換句話說,多元觀看、多層次的角度才得以面對。身處變動無常的當代社會,畫家僅能做的,即是將自身(人)在場、介入與參與等經驗注入於畫作,或藉由痕跡讓時間留存於其上,得以完成作品;接著作品成為可被觀看(審美)的客體,藉由觀者感官產生對話,使得觀者對作品有了感覺與想像,這想像隨即由大腦解讀成一種可(或不可)理解的語言與意象。在這轉換的過程中,我們可以了解畫家總和了感官經驗、過往學識與審美知覺去觀察描寫,雖說常人也做的到,但畫家可貴的地方即在於發現新的觀看方式,並搶先記錄下來、讓自身成為作品的首位觀察者。本文想先說明的,就是任何人對於風景畫都有自我看法,而其作法也有限制的地方,所以前述所謂「當代繪畫的風景語言」,其實只是唯名論的一個假借,試圖藉此定義找出風景畫的一種新可能性,以便和其他風格分別開來,也就是說,此說法並不能全然概括當下出現的風景繪畫,僅能代表一種我所認知的風景視野。本文曾提到當代風景繪畫裡有一畫種特具「唯心意識」,此類風景畫理念從一股對自然陌生又疏離的情感昇華而來,形式上表現出一種「去地域性」與「無歸屬感」的尋常風景面貌。如果我們再深入地探討,將它回歸到當代繪畫渴求文化記憶的特質裡,便會發現其中的風景語言有一個趨勢,即是自「去地域性」到「再地域性」 的步調裡,以下就以畫家鄭在東的作品來作一個說明。 以鄭在東早期七○至八○年代的作品來講,他描繪生活周遭,人物屋宇 、城市山煙與樹木橋樑等,這些景色置於台灣各個角落都說得通,看似十足的尋常景物,但細就其作品,便會發現某些...